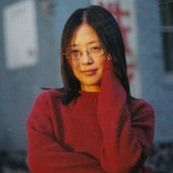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。 尤其是,听一个翻译工作者这么说。 我是多么欣喜啊,忍不住对着前方2点钟方向那个疲倦青年遥致一个微笑, 他穿一件手工编织的、上个世纪80年代风格的浅驼色毛线背心,和电脑蹙眉倾谈。
Author Archives: lily
九故事
因着旧译本遗失的缘故,刚拿到《九故事》新译时,就算译者名字里有李文俊,也只是淡淡的高兴。 去烟台的火车上看完第一个故事,《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》。最佳日子?记得旧译好像是更加简单响亮的“好日子”呢。“好”,岂不更好? 但是,好故事就是好故事,堂而皇之、无可辩驳的好,好到你拿在手里读着,译本也可以变得不那么重要了,完全不重要了,只余下好故事本身在闪闪发光,好故事照亮了你和周围,还有未来的日子。
天桥
朋友叫去看花鼓戏。 第一次有机会看这戏种,很是难得,戏是好戏,演员当真是好演员,在地方戏里藏卧着珍贵的身影,在舞台上展露出各自的声腔。 舞美不用说很下力气——其实不必下这么大工本——大戏的气势很足,结构都没有问题,但问题在唱词:有些粗简,有些不文,因为是很现实的题材,唱词里竟时有“傍上富婆”、“离婚痛苦”之类血淋淋的词汇,仿佛是剧作家慌手慌脚,来不及了,从“本埠新闻”里直接抄上去,墨迹未干似的。
别人的广告
如此新时代新年月,几乎非是当月新书才当得起新书的称号,否则就旧得羞于提起了,但自己看书,经常看的多半还是“旧书”,比方这本《爱看书的广告》,我不顾那么多,只当成新书来读。 从前的人给书作广告,谦逊平实,又华丽讲究,尤其是作者给自己的书写的广告,比如说下面这几段老舍的广告,抄录如下: 老舍给自己的书撰写的广告:
转贴思伽女史书评——《“前世”是“今生”的倒影》
“前世”是“今生”的倒影 作者:思伽 (《老戏的前世今生》 傅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定价:24.00元) 我是戏盲,却很爱看谈戏的文章。黄裳先生20世纪40年代写过本《旧戏新谈》,开篇即把当时的“评剧家”归为三类:一是内行的职业剧评家,二是捧角家,三是些傻瓜考证家。黄裳先生的那组文章,自然是在这三者之外的。 时光流转,六十余年逝去,又有了傅谨先生的新作《老戏的前世今生》。傅谨先生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,我想,以他的专业、学养、观戏经验,做“职业剧评家”是没问题的。但他偏不,不仅那三种“家”都不当,也不走黄裳先生的赏析道路,而是略过名伶、表演和掌故,去细抠那些古老的剧本。朱买臣、杨四郎、赵盼儿、阎惜娇,被他一讲,大家熟知的老故事,立时焕发出新意思。
七月,八月
一个多月前,父母带着小侄子来北京过暑假。 提前好几个星期,我就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大扫除、大整理。可是,父母来了,还是看出了一些问题,甚至是我得意的地方,也在繁华的假象下,一眼看出那深埋的危机。 比方说,我最引以为傲的绿色植物,他们一见就说,统统都要换花盆,更大的花盆。 换花盆的现场惊心动魄,一片狼藉,他们却一派从容,handle自如,在把天花板那么高的榕树从花盆里拔起来的那一瞬,我惊讶地发现,父母是对的:纠缠错综的根须盘据了整个花盆,几乎没剩多少土壤了——原有的土壤都被暗地繁殖起来的根须吃掉了,据说,这样下去,不出一年两年,就会突发危机,一夜颓败。
听人谈起
听人谈起他,在一间日料馆里。很大声地谈起他。 男的说:你知道LuXun吗……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……在仙台你知道吗? 循声望去,是一对年青的男女。男的稍稍轻佻,女的微微风尘。
相见欢
在碟店里见到Leonard Cohn的音乐纪录片 又忍不住拿起来唏嘘摩挲 虽然,在小妖的强荐下,家里已经有囤 但是,分不清是无聊赖的恋物,还是过度粘腻的怀旧